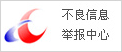種春天的人
那個總愛穿褪色藍布衫的女人,是我小學四年級的班主任。她姓陳,手指關節處常沾著粉筆灰,像星星碎屑嵌在皺紋里。
那時我們村小只有三間土坯房,漏雨的屋檐下擺著用磚頭墊高的長凳,她每天清晨第一個到校,用搪瓷盆接住瓦縫滴下的水,再踮腳把歪斜的課桌擺正。有次暴雨沖垮了教室后墻,她帶著我們搬來裝化肥的塑料袋糊窗戶,塑料布在風里嘩啦啦響,她笑著說是大自然在給我們伴奏。
她教語文時總把課本卷成筒狀,講到激動處就用卷筒輕敲自己太陽穴。有篇課文描寫火燒云,她突然扔下粉筆沖出門,回來時發梢沾著露水,從衣兜里掏出半塊燒餅:快看!云彩把燒餅染紅了!后來我才知道,她餓著肚子跑了三里地,就為給我們找塊帶焦糖色的燒餅當教具。最難忘的是她批改作文的方式——不用紅筆打叉,只在錯字旁畫個小問號,本子邊緣卻總粘著曬干的野花,那是她家后院種的指甲花,她說錯誤和鮮花都是成長的印記。
記得有個總尿褲子的男孩,她從不嫌棄,只是默默在講臺旁放個陶罐。有次男孩又尿濕了棉褲,她把自己織的毛線褲裹在孩子身上,陶罐里立刻響起嘩啦啦的水聲。我們哄笑起來,她卻嚴肅地搖頭:“聽見了嗎?這是黃河在唱歌。”后來她每天給男孩帶個煮雞蛋,直到他不再需要陶罐伴奏。還有個女孩總偷拿同學橡皮,她沒當眾揭穿,只是把橡皮雕成小兔子模樣:“看,它想跳回你鉛筆盒睡覺呢。”女孩自覺不對,遂改了這個不好的習慣。老師第二天帶來了用野草莓串成的項鏈,那是她家籬笆上長的,酸得我們齜牙咧嘴,她照樣戴在脖子上。
她改作業的煤油燈總亮到深夜,燈煙把她的臉熏得黢黑,像塊被火烤過的地瓜。有次有人半夜起來上廁所,看見窗紙上晃動著她的影子。她正用凍僵的手指翻作業本,嘴里含著熱毛巾取暖。后來我們才知道,她得了嚴重的關節炎。第二天她依然準時敲響鐵皮鈴,只是走路時總扶著墻,粉筆灰簌簌落在她磨破的布鞋上。同學們湊錢給她買護膝,她轉手就釘在教室漏風的窗戶上,說:“這是會笑的窗花。”
畢業前春游,陳老師帶我們去后山采野花。她教我們把蒲公英編成皇冠,用狗尾巴草做戒指。突然下雨,大家擠在破廟里,她變戲法似的掏出個鐵皮盒,里面是曬干的橘皮和話梅核。我們嚼著酸澀的橘皮,聽她講每顆種子都能長成大樹。雨停時,她蹲下身給每個孩子系鞋帶,藍布衫后背洇濕一片,像幅未完成的水墨畫。后來才知道,她那天發著高燒,卻把藥錢換成了鐵皮盒里的糖果。
最難忘的是她給輟學女孩補課的事。那女孩要照顧癱瘓的母親,陳老師就每天放學后繞三里路去她家,在灶臺邊支起小木凳講課。有次我去送作業本,看見她正用燒火棍在地上演算數學題。女孩母親突然抽搐,她立刻蹲下身給這位母親揉腿,轉頭她就對女孩說:“你看,這就像解一道人生的方程,你人生的答案就在這里。”后來女孩考上了師范,回校任教那天,陳老師把珍藏多年的紅筆送給她,筆桿上還纏著當年灶臺邊用的草繩。
畢業那年,她送我們每人一包野花種子,說:“等你們長成大人,花兒就開了。”現在每當我看見指甲花,就會想起她發梢的粉筆灰,想起她講火燒云時眼里的光。前年回村,聽說她退休后還在掃校門口的落葉,巧合的是,她依然身著藍布衫,被風鼓起時像面永遠不會降下的旗。
作者:董國賓
熱點圖片
- 頭條新聞
- 新聞推薦
最新專題

- 強國必先強教,強教必先強師。今年9月10日是我國第41個教師節,主題是“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譜寫教育強國建設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