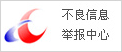悲歡的形狀
曾看到這樣一段話:人生的長度,長不過春夏秋冬;人生的寬度,寬不過南北西東;人生的高度,高不過藍天白云;人生的無常,無非是悲歡離合。
這話是說得很透,也很輕,像一片羽毛,落在心坎上,不痛,卻教人無端地怔住了。我于是擱下書,走到窗邊,想看看那被說盡了的人生,究竟是怎樣一副形貌。
窗外的天,是那種被秋雨洗刷過后、干干凈凈的藍,澄澈得像一塊巨大、冰冷的琉璃。幾朵白云,漫不經(jīng)心地浮著,是世上最逍遙的過客。它們那樣高,高得全然不理會人間的尺短寸長。我們一生汲汲營營,所奮力攀爬的,那些名利、夢想,壘起來,能觸到哪一片云絲的衣角呢?怕也只是枉然。人生的高,原來一早便被這天定了界限,我們只是在它無垠的底里,做著有限的夢罷了。
目光收回來,落在院墻根下。那里,一株老樹正不緊不慢地落著葉。春夏的繁華,它算是淋漓盡致地揮霍過了,如今只剩些疏疏朗朗的枝干,像一幅刪繁就簡的素描。一片葉子,打著旋兒,悠悠地、不情愿地,落在地上。它這一生,從萌發(fā)到飄零,所走過的路程,也不過是從樹梢到地面的幾尺距離。這便是長度了,被季節(jié)嚴格地規(guī)定著,逃不脫,也掙不破。我們總嫌一生太長,磨難太多,可若真拿去與這無言的天地一比,又頓覺短得令人心慌,仿佛才剛看清它的輪廓,幕布便要落下了。
至于寬度呢?我望向遠方,目力所及,是鱗次櫛比的屋脊,是蜿蜒至天際的馬路。我想象著路的盡頭,是海,海的那邊,是更廣大的陸地。南北西東,這便是一切空間的全部了。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長,可以乘長風,破萬里浪,足跡似乎能踏遍這顆星球的每個角落。然而,我們終其一生,真正能擁有的,不過是腳下立錐的一小塊土地;真正能看盡的,不過是窗前這一方被建筑切割過的風景。那更廣闊的天地,于我們而言,只是一張遙遠的地圖,一些他人的見聞。人生的寬,原來不過是一方精心構(gòu)筑的“樊籬”,我們自以為的縱橫馳騁,不過是這“界”內(nèi)一場略顯宏大的輾轉(zhuǎn)罷了。
高也高不得,長也長不得,寬也寬不得——這被框定的人生,其全部的滋味,便都濃縮在那最后一句里了:“人生的無常,無非是悲歡離合。”
這“無非”二字,說得何等淡然,又何等蒼涼。它將那漫天呼嘯的感慨,都化作了檐間一滴清冷的雨。可不是么?剝?nèi)ヒ磺懈∪A的修飾,人生的內(nèi)核,不就是這幾樣東西的交替與輪回么?
“悲”是有重量的,它來時,心便像浸透了水的棉絮,沉沉地向下墜,讓你覺得那秋日的藍天也似一塊鉛板,那遼闊的東西南北都成了無處可逃的荒漠。而“歡”呢,它是輕的,是羽毛,是彩虹,是夏日冰碎的叮咚,它讓你想飛,想歌,覺得天地霎時開闊,一切都可愛可親。可它又是倏忽的,你才剛要展顏,它已從你眉梢眼角悄悄溜走了。
至于“離合”,那便是這悲歡的形骸了。沒有離,哪來重逢的歡欣?沒有合,又怎襯得出別散的凄楚?它們是一對孿生的影子,永遠相隨。我想起童年時一個極要好的伙伴,那時我們形影不離,一同上學,一同在田埂上追逐蜻蜓,以為這樣的日子會直到地老天荒。后來他家搬走了,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城市去。送別的那天,我哭得撕心裂肺,覺得自己的世界缺了一角。那是我第一次嘗到“離”的滋味,是那樣一種尖銳的、具體的痛。許多年過去了,我們早已在各自的人生軌道上運行,偶爾在夢里,還會見到那個在田埂上奔跑、模糊的影子。這便是“合”留下的、一點溫柔的余燼,一點供你在“離”的寒夜里用以取暖的、微弱的星火。
這么一想,心里反倒生出一種奇異的平靜來。既然飛不到云外去,那便安心在樹下坐坐;既然走不盡天涯路,那便細心欣賞眼前的苔痕草色;既然逃不脫春夏秋冬的輪回,那便珍惜每一縷風,每一片雪。而那悲歡離合,既然是無常的常態(tài),那么,悲來時,便讓它沉沉地壓著,知道它總有泄去的一日;歡來時,便讓它輕輕地托著,曉得它終有消散的一刻。離時,且珍藏那美好的記憶;合時,便傾盡滿腔的真誠。
窗外的光景漸漸暗了下去,那原先明凈的藍天,此刻染上了晚霞的胭脂,又漸漸褪為一片溫柔的、鴿子灰的暮色。白云不見了,大約是回了家。遠近的燈火,一盞一盞,次第亮了起來,在漸濃的夜色里,像一顆顆跳動的心臟。每一盞燈下,大抵都上演著一幕幕悲歡離合的、小小的戲劇吧。
我離開窗邊,屋里已是黑黢黢的了。我沒有立刻去開燈,只在暗里坐著,覺得這被限定了長、寬、高的人生,因了這無窮無盡的悲歡離合,反倒有了一種充實的、可以觸摸的質(zhì)地。它不虛空,也不宏大,只是如此這般,真切地,在每一次呼吸里,完成著它自己。
作者:劉愛國
熱點圖片
- 頭條新聞
- 新聞推薦
最新專題

- 強國必先強教,強教必先強師。今年9月10日是我國第41個教師節(jié),主題是“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譜寫教育強國建設(shè)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