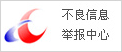理解靈魂對主體的凝視——讀阿來《云中記》
■陳培浩
《云中記》講述了汶川地震后,四川一個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傷亡一百余人,并且根據地質檢測,村子所在的山坡將在幾年內發生滑坡,于是在政府的幫助下,整村搬遷至一個安全的地方。然而村里祭師內心越來越不安寧,他總是惦念著那些死去的人,最終決定返回原來的村落,照顧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靈……
云中村是小說故事的發生地。這是一部飽蘸深情、莊嚴隆重的作品。阿來說,寫作這部作品,他一直是在莫扎特《安魂曲》的陪伴下的,在題詞中他也特別致敬了莫扎特,“寫作這本書時,我心中總回想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
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際,阿來拿出了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云中記》,整部小說如一部緩慢低回、痛徹心扉的哀歌,又是一部站在現實回望靈魂的頌歌。汶川地震給中國人留下難以忘懷的重大心理創傷,也是新世紀中國標志性的重大災難事件,阿來《云中記》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當代中國文學關于災難的記憶上升到了全新的靈魂刻度,他站在為民族創傷譜寫安魂曲的高度寫作,也觸及了現代性背景下故鄉的消逝和生命安居的困境等難題。
《云中記》的故事并不復雜,汶川地震中云中村遭遇災難,幸存者不僅要面對地震奪走親人生命或自身完整身體這一事實,還要面對地理裂痕使云中村不能居住,全村必須整體遷徙這一現實。在云中村整體搬遷五年之后,云中村“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祭師阿巴無法抑止內心對于故鄉亡靈的牽掛,重回云中村“履職”。小說以阿巴回到云中村的時間為線索和結構,從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寫到第六月,最后阿巴隨著云中村一起從山下滑下懸崖峽谷,成了用生命守望故鄉和亡靈的真正“祭師”。
汶川地震發生后,這一災難壓迫著中國人的心靈,很多人的創傷記憶需要文學的抒發和拯救,以汶川地震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并不少見,地震詩歌甚至在2008年成為一時風潮,其中朵漁的《今夜寫詩是輕浮的……》極受關注;其他體裁如李西閩的長篇紀實散文《幸存者》也頗受關注。地震之后,評論家謝有順撰文《苦難的書寫如何才能不失重》流傳甚廣,文章直面現實,又關涉著一個樸素的寫作倫理:回避苦難本身,將苦難書寫成溫情、勝利,都是一種寫作倫理上的失重。必須說,一場巨大的災難事件在要求著與之相匹配的文學書寫,我們能從災難中反芻出什么,也在很大程度上考驗著中國當代文學的內在精神結構。因為《云中記》的出現,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文學終于沒有愧對這個民族的巨大傷口。
文學如何書寫災難?很多書寫事實上都由“災難現場”所生發,阿來的關注點卻在“災難發生之后”。人們關注如何受難、為何受難、怎樣救災、如何安置等現實性問題——這些問題當然意義重大,可是對于文學來說,它要從這場沉重的災難中讀取的不僅是現實的、具體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在災難已經發生了十年之后。重新回看這場災難,很多現實問題的發生語境已經消失了,我們何以依然回眸?一個重要的理由或許存在于這樣的假設中:每一場重大的民族災難,都應該經由文學記憶的反芻而沉淀于民族精神成長的潛在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一個民族消化苦難的精神器官。假如所有的災難都僅僅被作為社會事件來處理,那我們的民族可能獲得社會的進步,卻不能獲得精神的沉淀和成長。
《云中記》是一部重靈魂的作品。這部作品呈現的一個最大糾葛正是現實與靈魂的糾葛,設若現實的人們可以完全砍斷靈魂的牽掛,那這部小說便不能成立,已經在移民村生活五年的阿巴就無需孤身回到云中村伺候那些地震后游蕩的亡靈,他也無需置外甥仁欽鄉長位置不保于不顧,死守已為空巢的云中村。
從唯物主義角度看,亡靈的世界顯然并不存在。但人類社會為何有如此強大的亡靈文化?一個重要的解釋是,將死亡視為生命絕對的結束,這是作為有死者的人類無法承受之重。因此,亡靈所勾連的彼岸世界便為現世提供了道德約束和精神皈依。人類的信仰系統發明了一整套祭祀儀式,正是人類托付自身存在的象征秩序。不過,作為當代作家的阿來,寫作《云中記》,其意味絕不在于提醒這一人類學的常識,而是通過阿巴執拗而帶著悲劇性的堅守與殉葬,激烈地提醒人應是有靈魂的存在。靈魂在小說中是一個泛指的概念,不僅是尚未消逝的亡靈,而是包括信仰、故鄉等等在現代即將消逝的屬靈之物。
現代是一個被全面祛魅的世界,《云中記》這番鄭重其事為靈魂復魅,不僅是紀念祭奠汶川地震中傷逝的亡靈,我想阿來的提醒更在于:災難固然創痛劇烈,但如果我們將死視為人生物性的消失而草草處置的話,才是精神災難的真正延續。哪一天我們像阿巴一樣,在鳶尾花的突然綻放中與亡妹的靈魂對話,在萬事萬物中感受到靈魂世界的唱和及應答,我們或許才能真正理解靈魂世界對主體的凝視,并懂得以何種善的倫理存在于世。
熱點圖片
- 頭條新聞
- 新聞推薦
最新專題

- 強國必先強教,強教必先強師。今年9月10日是我國第41個教師節,主題是“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譜寫教育強國建設華章”。